【專題企畫】
改寫生命故事,建構新城堡──敘事治療
採訪撰文 吳立萍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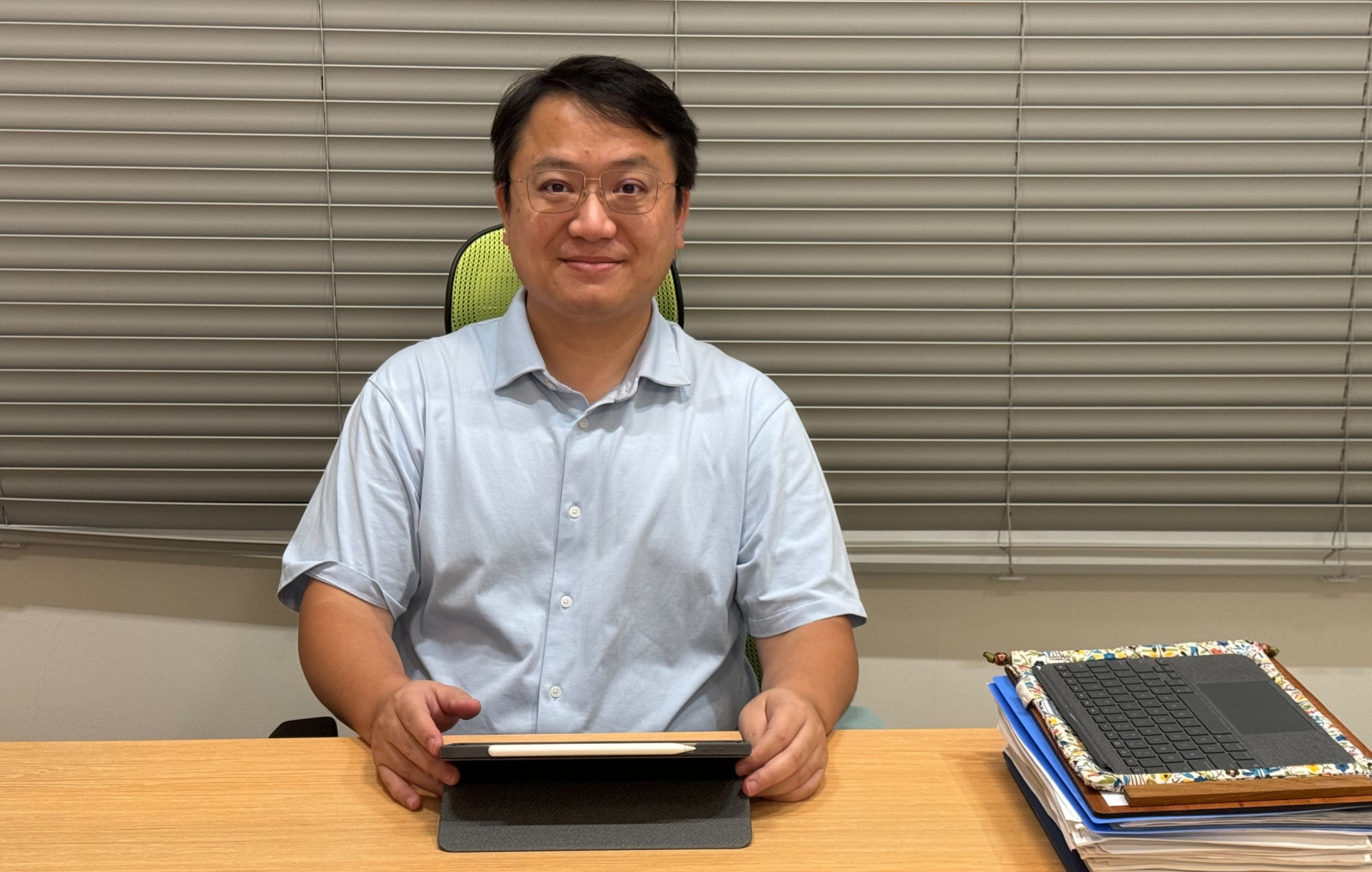
A小姐育有一子,不僅將公司經營得有聲有色,對外也給先生做足面子;對內燒得一手好菜,主理家裡傳統祭拜節日,努力做好妻子、長媳、母親和女兒的角色。對於婆家,不論多少時間、金錢及體力的付出,她都甘之如飴,表現得體周到,幾無可挑剔。父親臨終前很欣慰的說,「妳是家族的榮耀,我以妳為榮。」
然而,看似美滿的家庭,沒想到先生竟然外遇了,她非常震驚難過。婆婆和小姑們都站在先生那一邊,認為是她的錯。她想離婚,卻糾結於父親生前對她的期望及離婚女性的負面標籤等讓家族蒙羞,因而抑鬱不已……
她隱忍了兩、三年,終於開始尋求幫助,走進心理諮商室,接受敘事治療。
被主流壓迫的族群
敘事治療,就是透過述說自己的生命故事,以達到治療效果。也就是說,將治療比喻為「說故事」與「重說故事」,透過敘說、解構、再建構,激發賦予當事人未來希望的新版本故事(新城堡),屬於後現代心理治療學說。
「二十世紀末的心理治療觀念,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,這是一種哲學觀的轉移。」羅惠群解釋,敘事治療源自一九八○ 年代後期,由澳洲的Michael White 及紐西蘭的 David Epston 發展出來。起因於社會存在著所謂的「主流」,如富裕、父權、種族、異性戀……等霸權,只要是「非主流」就會被貼上疾病的標籤。也就是說,只要有主流存在,就會有被主流壓迫的族群。
在現代主義的觀念下,認為世界只有單一真理,比如人不憂鬱才是正常,所以當一個人被診斷有憂鬱症,表示在精神醫療系統裡,已經被貼上疾病的標籤。因此,現代主義的治療師,治療的目標就是幫病人改善及修理憂鬱。
敘事治療則是後現代主義的治療方式。以A小姐來說,她的憂鬱來自於傳統父權社會性別不平等的壓迫,不是她有疾病,也不是她的問題,所以要協助她重新找到定位,不再受到主流價值觀的壓迫,也就是要幫她解構、再建構。
故事的解構、再建構過程
「她其實想離婚,但『爸爸的榮耀』 是她無法跨越的框架。所以我要幫她解構,慢慢拆掉這個框架, 讓她接受榮耀的定義不僅限於傳統的認知, 要相信能夠活出自我也是一種榮耀。」羅惠群表示,這不是一、兩次諮商就能達成,而是需要來來回回很長一段時間。解構之後,治療到中後期階段,他再協助A小姐慢慢接受「帶著一個孩子的離婚媽媽」這個新的角色生活下去。所以,要協助她把該切割的切割掉,比如婆家的人;該整理的整理好,比如原生家庭的整理。一道道關卡突破了,她才能真正接受自己是個離婚的婦女。

他形容,這就像是一個人從小到四十幾歲,一路以來接受的觀念和制約,構築了四十幾年的城堡,堅不可破。因為從出生以後,我們就開始建構主流意識,大人會灌輸你男生穿藍色、女生穿粉紅色,男生玩機器人、女生玩扮家家酒……等等根深柢固的觀念,導致過去的故事不可能馬上就被解構完,只能一步步慢慢遠離。
「新的故事也需要慢慢給予養分,才有機會壯大,畢竟我們仍然生活在婚姻成功才是幸福美滿的主流中。朋友或其他人可能時不時會關心:你離婚了還好嗎?或者看到類似的影片情節時,突然感到情緒低落;因為主流認定離婚是不好的或是傷痛的事。」羅惠群表示,幫她再築的新城堡,起初當然無法和四十幾年構築的城堡抗衡,可能有時還會部分垮掉,但就是在不斷來來回回構築中,愈來愈厚實;最後雖然社會的主流還是在,但因為新的城堡已經很堅固,可以讓她不再受主流的影響制約。

局外見證人的回饋
有一位國中男生B同學在學校受到霸凌,他害怕上學,媽媽支持他參加學校的自學方案;但爸爸不同意,覺得男生應該要堅強,不能因為這些事就不去學校。他感到很憂鬱,也很氣爸爸為什麼要接受公司的調派,突然就離家到國外工作。學校老師察覺到他的負面情緒,透過與家長的訪談了解原因,並將情況告訴當時與學校配合進行青少年心理諮商的羅惠群。
在敘事治療過程中,羅惠群發現他和爸爸的關係其實很好,爸爸會帶他出去打球、運動紓壓,所以當爸爸突然被調派國外,他很不能適應。
「我先幫這個孩子做一點點解構,不要卡在一定要入校、入班上學的主流。再視訊連線爸爸,一家人一起聊一聊,了解彼此的想法,爸爸擔心什麼、媽媽擔心什麼、小孩自己的擔心又是什麼?所有人各抒己見,其實就是重構。」羅惠群表示,他們以前不會討論這些事情,孩子到了時間就去上學,上一整天課、下課再到課後輔導班,都是固定模式,從來不會討論現行的教育體制是不是真的適合孩子。
「有時候我會用方法,例如當其中一人講話時,其他人不要插話、不要回話,就是專心聽。然後我會問其他人,剛剛聽到了哪些內容?我就可以了解說話者的觀點在其他人眼裡如何,從中找到差異,再幫他們做協調。」羅惠群表示,其實就是幫大家帶出更多共識和對話的機會,因為每個人容易各執己見,在家裡可能不好談,換一個溫馨的諮商環境,比較不會受過去的情緒影響。
後來B同學終於在雙親都理解及支持的情況下開始自學。達成家庭共識之後,再邀請他的同學,包括也在自學的同學或班級好友,還有他的家人,爸爸、媽媽、阿公、阿嬤,以及學校老師等,一起來參加在諮商所舉辦的派對,並頒發證書及獎品,慶祝他建立了一個新的小城堡。
敘事治療經過解構、再建構之後, 新的城堡還要有「 局外見證人」(outsider witnesses),這是由Michael White 提出,透過身邊親友對當事人故事的傾聽,回饋給當事人所不知道的優點及表現,讓他能將這些回饋融入對自我的描述,增加看待事情的觀點。
「透過局外見證人,可以幫助當事人改變看世界的方式。我們會舉辦活動,並頒發證書給當事人,尤其對於青少年來說,這是一種實質的回饋和支持。」
「 這些生命故事, 能引發我更多的內在思考, 這些反思(reflecting),不是專屬於敘事治療,而是後現代的對話歷程。我聽到的部分,會回到我的生命裡再重新搜尋,觸發我生命當中某一個悸動;所以,這些生命交流對我來說都是有價值的,而不只是用來幫助對方解決問題。」
許多人願意來分享他們的生命故事,這些都是善緣,羅惠群很珍惜及善待這個緣分,希望在敘事治療的方法下,可以為更多人找到自己內在的需求,構築一個堅固厚實的新城堡。
所屬出版品
生命季刊178期

